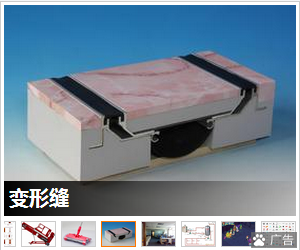94红磡演唱会,只是冬天里的一把“虚”火
94红磡演唱会,冬天里的一把“虚”火
如果崔健是最早为中国摇滚注入人文思考和现实批判的歌者,那么唐朝是最早将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融入中国摇滚的乐队。1994年12月,窦唯、何勇、唐朝乐队等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这就是后来被神化的“红磡演唱会”。在魔岩文化前负责人张培仁的回忆里,唐朝乐队的风格在当时非常前卫,深刻且犀利,与当时的流行音乐背道而驰,公司选择透过唐朝来扩大新音乐的边疆。“我们在《中国火1》里已经把唐朝当成一面旗帜,如果这个旗帜能够成功,那就表示解放了很多的年轻人对音乐的想象。”
唐朝乐队的野心与局促
2019年6月30日晚,唐朝乐队作为压轴乐队结束了在福建莆田的演出,45分钟表演时间里,老歌占了七成。今年是唐朝乐队成立的第三十年,乐队迄今发了四张专辑,但被人们记住和传唱的,只有第一张专辑,或许对于更资深一点的乐迷来说,有时候也会加上第二张《演义》的部分作品。
第二张专辑是唐朝乐队的分水岭——唐朝乐队的野心与局促都体现在那一张里,专辑发表于1999年,乐队彷徨在自己世纪末之梦的边缘。他们不仅想延续《梦回唐朝》里塑造的盛世豪情,还要将这种豪情与现实对接,去扩大幻想,结果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加入了现代的背景,唐朝乐队自己的美学系统被破坏了,听众的观感也开始跳脱了。主唱丁武说,那张专辑里的一些歌,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演出过。唐朝乐队没有将神话连载进21世纪。“新世纪以后,唐朝乐队的专辑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了,后来的唐朝是一个正常的乐队,作品水平什么都很正常,也都很唐朝,就是没有惊喜,对于一个乐队的发展来说,这是好事,对听众来说,唐朝失去了自己的唯一性。”乐迷小孙说。
文化上的认同与个体意识的觉醒,都在激发90年代年轻人的创造力,处在转型期的社会,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的土壤。摇滚乐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与先锋小说、诗歌,第五代导演作品几乎同时成为新时代新精神的刚需。魔岩文化的另一位创始人贾敏恕担任了唐朝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他最初接触中国摇滚乐时便感受到了那种涌动的力量,“认识之后我就把琴送给他们了,自己再也没弹过琴,因为(相比之下)没有意义”。
音乐制作执行的是工业标准,需要理性推动,在制作唐朝乐队第一张唱片时,贾敏恕的工作是将唐朝乐队拥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是他的工作要求,但完成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又超出了他的经验。“那些都是血液写的歌,不是生产的,是喷涌而来的,我现在很少说过去,说出来别人也把你当骗子,但在那时候,大家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情怀。”贾敏恕记得乐队拍摄MV时,在黄河边,面对泥沙俱下的奔腾,几个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流下了眼泪。
在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发表之前,代表作《飞翔鸟》已经在《中国火1》里率先面世,在大多数音乐人还处在模仿西方摇滚乐的阶段里,唐朝率先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西方的肌理,东方的内核;动听的旋律,恢弘的编曲。这个理念也完整贯穿在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里。摄影师高原说,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在叫好,“无论我对他们有什么个人意见,必须承认他们第一张专辑确实牛,虽然跟流行明星没法比,但在摇滚圈里,唐朝那时候已经(火)到头了”。在高原的印象里,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即使是几年后集体发片的魔岩三杰,也都没有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再一次见到相似的场景,是汪峰走红之后,“汪峰是更牛了,他有保镖”,高原半开玩笑说,“后来我们看一个人牛不牛,就看他有没有保镖。”
唐朝乐队是张培仁到内地后认识的第一个乐队,已故贝斯手张炬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从唐朝乐队开始,魔岩文化将野蛮生长中的中国摇滚乐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语境。在高原看来,魔岩当时的理念至少领先内地二十年,“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一些东西了,乐队录音的时候,拍MV的时候,我会去拍一些照片。”高原是魔岩文化的摄影师,一百美元的月薪,魔岩从来没有给过她具体的拍摄任务,她在创作上拥有绝对的自由,那时魔岩文化的宣传物料,都是直接从高原作品中挑选使用。
2015年,高原发表摄影作品集《把青春唱完1990——1999》,副标题是《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作品集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生活状态,高原说拍摄时没有明确的作品指向,那时大家天天在一块,作品只是随心随手的记录。或许正因如此,这些瞬间在今天看来显得格外生动。作品集发表后,在小范围引发了一场怀旧——这些很多早已成为浪潮弃子的中年摇滚人,在他们自己的年轻时代,也曾有机会改变潮流的走向。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的评论,这是中国圈子文化的一个缩影,荣光都是内部加冕,他们只是幸运地出现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上,在时代的横截面上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记号。
工业化使乐队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