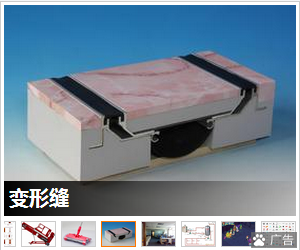基于价值观的改编 才是戏曲最珍贵的动能
我对戏曲算外行,对于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各个剧种,只能看看热闹,不敢谈其门道。但还是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当年看曾静萍的《吕蒙正》,戏是真好,尤其是“过桥”“入窑”两折,形体之美、唱腔之雅、传情之透彻,令人赞叹,不得不服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是真好,其美感的仪式化和节奏都值得传承。但回到文本和价值观,像《吕蒙正》这样的老戏,也逃不脱“大团圆”的传统范式,寒窑里十载等来了丈夫高中,然后一家人高高兴兴“战胜”了世俗压力,从此幸福地在一起,实际上还是屈从了“功成名就”的编剧铁法。
其实,现代人不大愿意看戏曲,一是因为节奏慢,二是在价值观上很难找到共鸣。戏曲的改革阻力历来是很大的,一方面有多年形成的“规矩”,另一方面应着各路“需要”新编了大量现代戏,各种舞台手段胡乱介入,弄出许多应一时之景和应评奖之需的作品,既经不起推敲,也没有传世价值。
但事实上,即使是最经典的戏曲作品,真的要传世、要与当代观众建立连接,也是需要不断重新诠释的。正如莎士比亚的剧作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艺术家的二度创作中,都有可能被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解读,但这种改编,并不影响其经典性。也恰恰是这种不断的改编和呈现,保留了其“与时俱进”的动能和经典性,让它永远是活的戏,而不是死的文本。
近日在深圳保利剧院观看的香港艺术节委约、制作的《百花亭赠剑》(毛俊辉导演,更新版),就是这样一部由骨子老戏新编而来的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新戏,剧目在原粤剧《百花亭赠剑》基础上改编而来。这部香港著名编剧家唐涤生(1917-1959)为“丽声剧团”编写的作品,由名伶何非凡等担纲,1958年10月首演,距今已60年。文本可上溯至无名氏明传奇《百花记》,全本剧本亡佚,散出见于明清诸多戏曲选集,以青阳腔或昆腔演唱。徽班进京后仅常见《百花赠剑》《百花点将》等折子戏的演出记载,北方昆曲《百花记》十二出已是明传奇的改编本,结局大不相同。1958年程砚秋为言慧珠、俞振飞整理《百花赠剑》,出访西欧,成为中国戏曲载歌载舞的范例,《赠剑》至今仍是戏曲舞台上最常演的一折。
毛俊辉导演的新编版《百花亭赠剑》全剧最重要的文本变化,是改变了原有的大团圆结局,反贼安西王之女百花公主和“叛徒”江六云这对处于困境中的夫妇,最终抛开一切世俗的功利与诱惑,逃出宫门,追寻自由快意的平民生活,剩下锢于功名利益的安西王、邹化龙、太监等打成一团,而这对夫妇挥着马鞭从舞台上跑到舞台下的观众群中。
改变故事的“结局”容易,但在达成结局之前塑造出完整的人物和构建达成这一结局的合理逻辑链条,则需要更大的功夫。所以这一版《百花亭赠剑》,一直在讲情讲义,注意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展现其情感。百花公主自幼被当成“花木兰”来培养,练就一身武艺,刚直不阿,只为有朝一日能够辅佐父王拿回皇位;江六云才高艺精,风流倜傥,背负朝廷监控之责,以佯疯之举被招入安西王府内当参军,但遇见百花公主后双双心生爱慕,最终为了爱情夜过敌营,找姐夫邹化夫求情,希望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百花公主重义,却在最后关头被父王“出卖”,要求她交出丈夫换取全家的平安和名利;江六云重情,却被想以平叛邀功的姐夫利用,成为将要献出的“祭品”。
在这一复杂的剧情与情感纠葛中,另一位更具悲剧性的人物江花佑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战乱中与丈夫失散,被公主收留后,情同姐妹。她一心侍奉公主,却偶然遇到了混进宫中的弟弟江六云,在想要保护弟弟的同时,她也同样思念敌营的丈夫邹化龙,偷了令牌出宫想要见丈夫一面就回宫的她,却被灌醉,邹化龙用她的令牌带人打进宫中。对丈夫既爱又恨的她,一方面念公主善待多年的情义,另一方面希望保全弟弟的性命,将安西王和邹化龙等商量的“献祭”方案告诉了公主和弟弟,促使他们最终逃脱,但她却不得不面对邹化龙最终死于混战中。这条人物线索是新版中的重点刻画,作为一条相当重要的辅线,强调了像百花公主一样的女性,对情感的执著和内心的真诚。
经过改编,在这部戏里,每个人的性格和命运都开始变得复杂和有肌理,而不是简单的面具化和符号化;他们的每一次举动,都是因为内心的情感和欲望所推动,而不是由一种编剧定式来指挥。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会真正地融入剧情,关心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走向,同时也会思考如果是自己处在他或她的位置上,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同理心和人物情感的有机化,恰恰是古典戏曲最需要的当代共鸣。